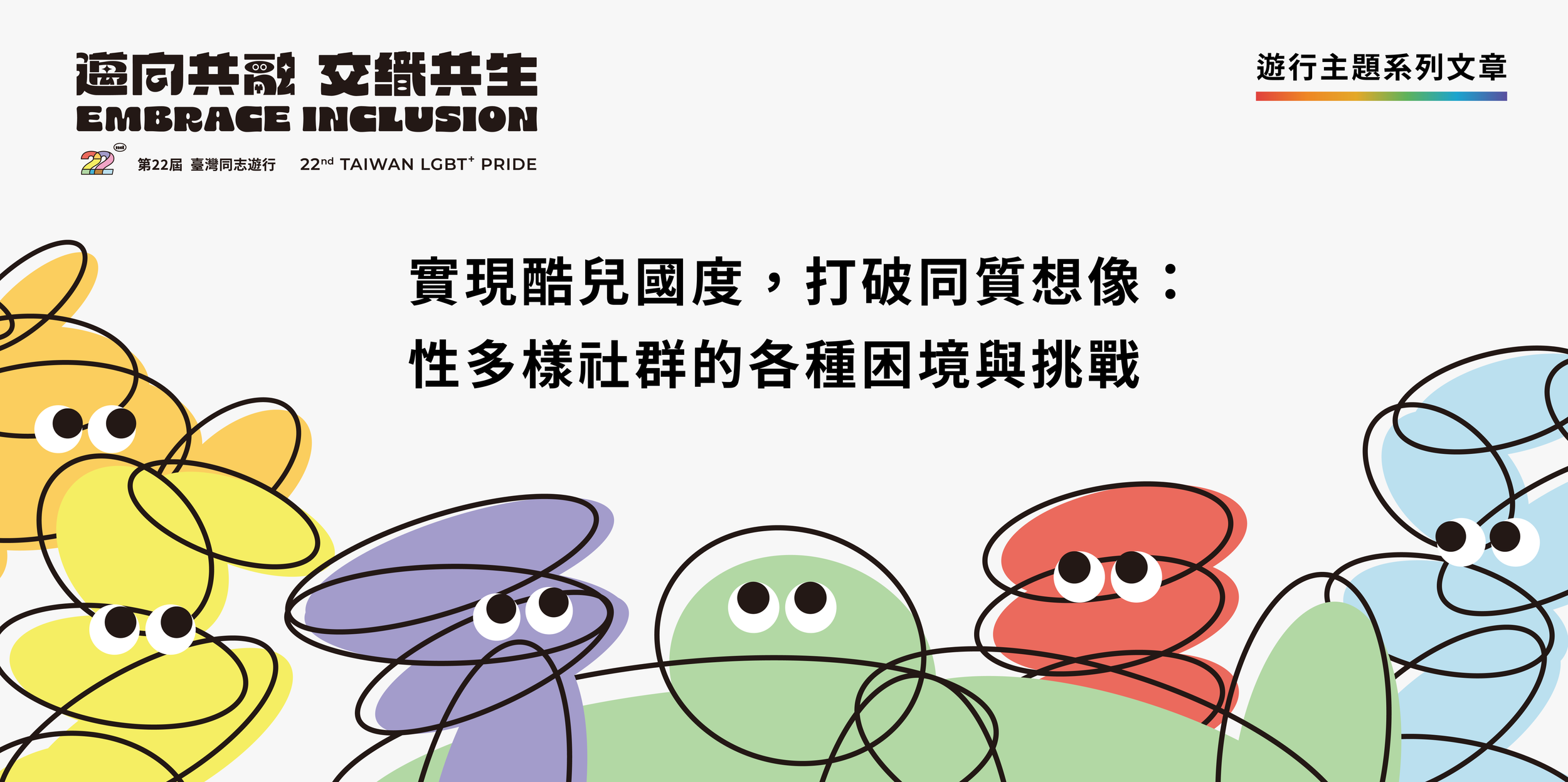實現酷兒國度,打破同質想像:性多樣社群的各種困境與挑戰
“We’re here! We’re Queer! Get used to it!”
上述口號起源於1990年,當時社會仍然對於多元性別沒有任何概念,而將性多樣社群貼上「淫亂」、「疾病」的標籤,使得社群遭受嚴重的壓迫與歧視。因應主流社會對於社群的挑戰,同志們開始起身爭取權利,期待能夠創建平等的社會制度及各種社會上健全的生活保障。然而在當中有一群人認為,將性多樣社群與異性戀視之平等並非運動的最終目標,而是是正視社會對於性的污名及歧視,期待打造一個承認各種性實踐、性偏好的社會。於是,同志運動期待透過顛覆性的字眼扭轉社會對於社群的想像,原意為「怪胎」的Queer(酷兒)即是誕生在這樣的脈絡下,意指「我們就是怪胎,我們也在社會上」,企圖讓大眾承認更多種性生活的樣態,同時理解、欣賞個體的獨特生活方式,不帶有批判性的讓每個生命都可以和平、有尊嚴的活在世界上。
Queer Nation的想像有沒有具體實踐過,又或是說,這樣強調多元、共融的形式如何可能?探究同志運動的歷史,最可以體現的實例或許是美國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1970年代,在同性戀仍然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精神疾病」的年代,石牆酒吧因為有著黑手黨的庇護,而凝聚了各式各樣的性多樣社群──像是變裝皇后、跨性別者、無家者、HIV感染者及性工作者,其中多半擁有黑人,拉丁裔的身份,他們不分階級、種族、性別及各種身份,得以在同一塊區域生存,同時尊重並擁抱彼此的差異。
石牆暴動的「漂白」歷程
隨著對於石牆酒吧不合理的盤檢趨於頻繁,性多樣社群與警方的關係也越發緊張,進而開啟同志運動第一次反抗的歷史:人們站出來抗議,訴求不再因為自己的身份而遭受到騷擾甚至逮捕,當時挺身而出的有色酷兒、HIV感染者、性工作者,他們期待有一天,社會能夠包容每一種個體樣態,而不會因為身份而遭到社會的排除。
當年及各種多元且邊緣性多樣社群所聚集的石牆酒吧,今日變成所謂「彩虹觀光」必去的景點,然而,卻只有經濟條件優渥、享受運動成果的白人男同志才能負擔得起高達16美元的長島冰茶,各種挺身而出的邊緣性多樣社群,因為負擔不起當地的高物價,已不復存在於石牆酒吧周圍。諷刺的是,紀念石牆暴動歷史的電影《石牆》中的主要角色皆由白人男性擔任,無視當年運動的主要發起、規劃者皆是有色族群、跨性別者等多元社群,此舉引發了軒然大波,甚至引發了各種性多樣社群的強烈抗議。
為何原本屬於有色酷兒的故事會被重述、甚至扭曲為白人的生命經驗呢?事實上,身為「同志地標」的石牆酒吧,需要一個好的行銷手法,讓這段激昂的歷史能讓更多人所知曉,進而創造更多的商機與熱論,於是,所謂單一樣態並且以白人男性為主的同志社群故事與經驗被植入了格林威治社區,讓主流接受的同志生活型態被保留而傳頌。
從上述可得知,但我們談及「多元」的價值時,仍然還是十分侷限且單一化,甚至落入到原有的二元化窠臼當中,例如:當性別身份牽涉到其他標籤時(如:黑人、HIV感染者),不但無法被社會所允許,甚至會面臨到更嚴峻的處境。同時,透過大眾媒體、影視作品的傳播,即使讓主流同志得以被看見,陳述的故事大多卻呈現了某種社會的既定刻板印象(例如陽光、陽剛、時尚、對於穿搭很有想法的順性別男同志),而無法看見社群當中彼此的差異以及困境。綜上所述,在性多樣社群當中,我們仍然還是劃有某些莫名的規範、界線,以至於社會距離落實「多元」、「共融」,還有好長的一段距離。
性多樣社群內部的歧異與挑戰
回到台灣社會,社會的既定框架與期待仍然存在,影響你我的生活樣態。即使透過同婚賦予性多樣社群法律上的保障,同時社會也理解到性多樣社群的存在,進而將他們納入社會制度當中。然而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對於多元族群存在著歧視與壓迫:2024年10月6號,有網友在Dcard上匿名發表《致想談戀愛的0號們》一文,列出12點戀愛建議,建議男同志0號(在性交過程中的被插入方)不應該展現自身陰柔樣態,內容包含「我們是男生,不喜歡有屌的女人!」、「請你們正常男生樣,自然就有1號喜歡你們了!」,此文正是體現出社會對於各種性別角色、氣質仍然存有許多規範,進而讓性多樣社群被迫在既定社會框架內選擇自身樣態(在性交當中的被插入方要陰柔、女性化,而插入方應當為陽剛、男性化的氣質)。從酷兒(Queer)的觀點去審視這些議題,我們即使高舉著「做自己」,真的能讓每個人成為「自己」嗎?我們面對、承受的仍然是對於彼此的不理解,也無法接受與自身不同的生活經驗、習慣及期待。進而抹滅了更多生活嚮往的可能,甚至讓歧視與污名得以持續。
看見異質性,擁抱多元共融價值
從石牆革命「漂白」的歷程,再到性多樣社群內部的歧異與挑戰,我們發現到了2024年,社會雖然得以看見同志,但卻對於社群內部擁有著同質化的想像,而忽略了更多樣化,且不被社會理解、看見的個體:大眾無法同理身為性多樣社群個體獨特的型態與各自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甚至以道德枷鎖、刻板印象與污名加諸在「非主流同志」身上,我們無法聽見各自的需求,也可能讓社群內部的個體們需要獨自面對這些束縛與困境,這不只無法提升同志社群的整體權益,甚至無疑是對於邁向多元社會的最大阻礙。
從酷兒(Queer)的觀點來審視,「做自己」不只是代表著承認同志社群,更不僅僅是看見多元群體的存在,而是更細緻的讓每個「自我」擁有訴說自身生長背景、生命經驗、族群、生活樣態的權力,進而在理解、同理對方處境的前提下打破既定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達成共融、共好的社會想像。
參考資料
卡維波. (1996). 什麼是酷兒?. 性∕ 別研究第三、四期合刊《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 32–34.
楊鈞傑. (2022, August 18). 當年石牆暴動的有色酷兒,如今被「漂白」埋葬在社會制度與都市記憶裡. Thenewslen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0960
(撰文/誠雲 編輯/RC、鴻軒、戴佑勳 引言撰文/詹奇奇 引言編輯/大嬸、小白 圖片設計/Boris)